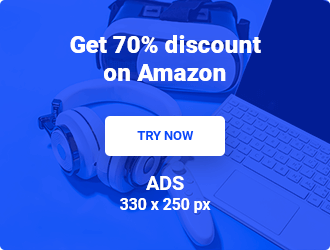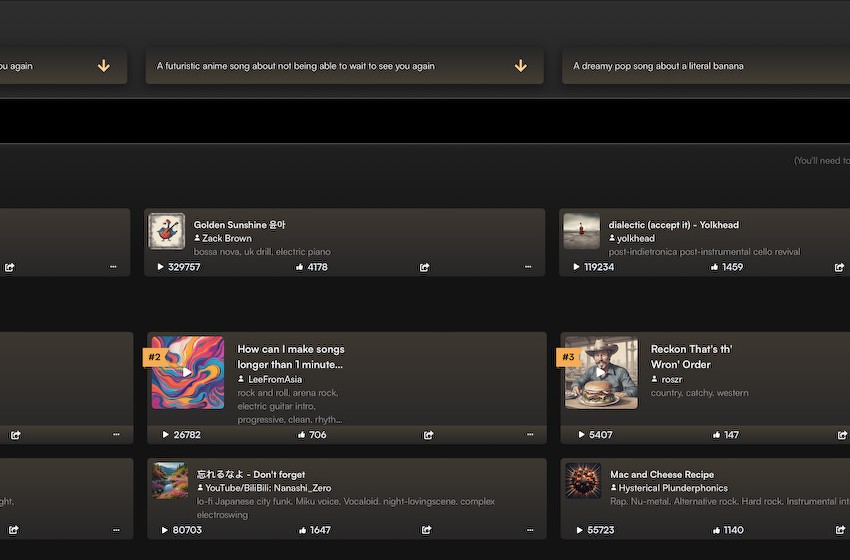观影|叙事、建构与共同体——《长安三万里》编创传播历程中的三重意义
要说当前院线热映的第一现象级电影,非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莫属。截至7月16日,《长安三万里》在上映仅仅9天的情况下,累计票房已达5.75亿元,打破了过去三年暑期档动画片档期票房纪录;而这种热映的状态仍在继续,笔者7月14日晚上在南京最为普通的老牌电影院——和平影城观看本片时,影厅的上座率就高达七成以上,有一多半都是家长携孩子一起过来观看电影。在前期宣传不多、且不太被看好的情况下,《长安三万里》何以成为今年暑期档的现象级电影?在本片的编创与传播历程中,有哪些值得玩味的时代节点性信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笔者尝试为大家简述一二。
第一重意义——叙事

作为以唐诗为主题的历史题材电影,选择什么样的叙事视角,将直接关系到影片传播效果的成败。有意思的是,影片并没有采取诸如李白、杜甫这样的唐代顶级诗人自述的方式展开叙事,而是通篇都以另一位名气没有那么大的诗人——高适的回忆进行叙述。高适的第三方视角叙事,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高适是唐代诗人中、在仕途上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在一个全民皆诗、而诗歌写作能力也成为官员能力的重要考量标准的时代里,以最终官职最高的诗人之一——高适的视角记述,显然能够具备大众意义上的说服力;第二,由于高适的名气并没有李白、杜甫那么大,这种去声名化的诗人记述视角,很容易让观众们有代入效应,能明显拉近观众与李白、杜甫等声名赫赫的诗人的心理距离,仿佛自己身处那个时代,也有机会跟他们称兄道弟;第三,高适一方面仕途堪称成功,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又跟各位知名诗人之间、都有着交往经历,以高适的视角展开记述,一方面能有盛唐开元时期景象的大历史观照,另一方面也能成功串接起诸位诗人的群像。应该来说,这样的记述视角是独具匠心的。

再进一步而言,高适之于开元盛世的追忆,也并不是完全散点化的,而是始终以他跟李白数十年来的友谊作为主线展开。尽管这样的友谊叙事带有很强的艺术化处理成分,但基于电影艺术的叙事而言,它一方面让影片的叙事推进不至于过分散乱,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对这两位交游极广的诗人的互动关系的记述,带出和串接起当时几乎所有的代表性诗人群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串接并不只是包括代表性诗人及其代表性作品,甚至这种代表性诗作里提及的重要人物,也同样出现在影片的记述当中。无论是李白名篇《将进酒》里的岑夫子、丹丘生,其另一首名篇《赠汪伦》里的平民友人汪伦,杜甫代表作《江南逢李龟年》里的乐师李龟年,都以写意而极具浪漫色彩的人物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这种对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人与诗作中人物的形象化演绎,实在能激发大家的广泛共鸣。

最后,影片里的盛唐叙事,是采取身处安史之乱之中的节度使高适的温情回忆展开的。当时的大唐王朝,内有尚未平息的安史之乱,外有吐蕃入侵长安都城,这种于国家内忧外患之中、追忆盛世景象的叙事方式,多少能跟经历了疫情三年后,大家普遍渴望复苏和安定的社会心理一拍即合。于是借助于电影院里的集体化观看,影片里对盛世景象的追忆,在当下类似语境的公众共鸣当中,实现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生成,值得玩味。
第二重意义——建构

作为艺术作品,电影之于历史事实的处理,总会进行适合于影片主题表达的重新艺术化处理与相应建构。《长安三万里》在唐代诗人与诗作的群像建构上,有着祛魅与赋魅这两个不同方向的艺术化处理。
之于祛魅,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片中的主人公之一——李白。对于习惯了教科书里“诗仙”李白的定位的很多观众来说,电影中李白形象的轻浮、孟浪与张狂,是具备一定程度上的陌生感与挑战性的。然而如果读过一些关于李白的严肃传记的话,就会明了片中这样的李白形象,恰恰是对历史上真实的李白的一种去神化与去经典化的还原。无论是热衷于“干谒”以求功名,还是浪荡张狂而不识人情世故,实际上都是这位伟大诗人人格气质中的一体两面——因为追求卓越不凡,而渴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因为浪漫、天真、想象力丰富,而对世间俗务不甚了了;因为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强烈的自我表达冲动,而导致个人性格的自我化、对朋友和他人的感受关注较少……喜欢李白的诗意与浪漫,其实就必须接受他的天真与自我,而后者往往在这位诗人荣登“诗仙”宝座、进入经典化殿堂之后,被选择性的遮蔽与忽略。从这个角度来说,影片之于李白的人物形象建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步。当我们看到顶着大肚腩、酒醉不醒的中年李白在跟高适相扑过程中的笨拙与滑稽之时,我们的会心一笑,就是让这位“经典”诗人,重新走入跟你我一样的烟火人间。

有祛魅,自然就会有另一个维度上的赋魅。由于影片以盛世唐诗作为主题,这就决定了编创团队所选择的诗人及其作品,都会是围绕开元盛世的这一浪漫化建构来展开的。就影片中选择表达的诗人与诗作来说,这种之于开元盛世的浪漫化建构,大致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都城长安的繁华景象为中心,歌颂大唐王朝之于国民、甚至周边国家的巨大影响力与向心力;二是以盛世繁华景象为中心,呈现开元时期的国富、民乐、山河安定;三是以盛世之中的文人群体为聚焦,呈现开元时期以诗人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群体的自由、肆意与浪漫精神。借助于这样的三重建构,一个以唐诗为媒介的开元盛世景象,就通过出色的动画技术、影像塑造与声画同步,立体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人心存神往。
与这种浪漫化建构同步进行的,就是另外一些层面的选择性忽略。比如影片中,杜甫第一次出现时还是孩童,后来再出镜时,也不过是青年形象,在影片当中,绝对是以配角的形象存在;影片引用到的他的诗,也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跟盛世景象相匹配的诗句。杜甫创作的以“诗史”著称的反映平民百姓生老病死苦难的众多诗作,在影片当中处于缺位状态,这绝对不会是一种偶然,而是影片编创团队为了突出盛世建构而作出的选择性放弃。与此相对应的是,影片的叙事中心,也都是围绕盛唐代表性诗人展开,那些以平民为主题的诗作,连同诗作里那些重要的平民形象,也一概在影片当中难以一见。这样的去社会史书写的精英视角叙事,跟影片盛唐盛世建构的创作主旨,可谓是一脉相承。而对这样的叙事建构作何评价,就属于见仁见智的事情,留给读者们自行判断。
第三重意义——共同体
按照罗兰·巴特的界定,作品的意义,是由受众与作者共同建构生成的。因此考察《长安三万里》的热映原因,我们不能只把目光停留在影片的编创环节,而要以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同样注重考察传播环节中受众的意义生成情况。
如前所述,影片采取的于国家内忧外患之中、追忆开元盛世的叙事视角,自然能够跟疫情三年过后、大家普遍求治求安的社会心理一拍即合。这种于“巨变之年”、纵情勾勒盛世之追忆与想象的浪漫化影像处理,是对于大变之后的当代中国观众最好的精神疗愈,也能够给在复苏之年中奋斗的人们以希望和信心。

除此之外,影片之于盛唐景象下“另一面”的真实描绘,也能够激起当下观众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比如影片中的盛唐,尽管已经推行科举制度,但世家门阀之于社会流动和社会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一时间仍然难以撼动。李白因为是商人之子而屡屡报国无门的景象,实在让人扼腕叹息。这样的影像描绘,在阶层固化的普遍性社会焦虑的心理背景下,自然也能够激起观众的普遍共鸣。而即便浪漫、洒脱如李白,也需要结交权贵以求功名,这种谋求向上流动的强烈愿望,跟如今所谓“内卷”“鸡娃”的功利化、实用化的社会竞争心理之间,也存在着不言而喻的不谋而合。
跟上述工具理性化的社会心理共鸣相比,影片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成功激发起以唐诗为媒介的古典文化的超越性共同体记忆。影片结尾之处的台词,着实将其立意提升不少。“只要书在、诗在,长安就在”——这样的动人话语,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之大者”语境下,就是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文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温与大力推广,重新构建起一个坚实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护佑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坚毅前行。

基于这样的宏大关怀,《长安三万里》的问世与热播,绝对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现象。它跟央视和地方卫视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优质文化类综艺节目,跟各大主流媒体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报道、传播与推广,跟社会公众对于古典文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越发热捧与传播一起,都是“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发受到重视、维护与大力传播的举国图景的如实呈现。如是,电影院里出现的孩子们同诵唐诗、家长们为理解了唐诗中的“中年危机”而感动不已的场景,正是《长安三万里》在切合时代重大命题的背景下,于传播过程中对“家国一体”的生动诠释。这样的作品,即便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与不足,也仍然是值得大力推荐、并且前往电影院从容观赏的。
2023年7月16日上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23年7月20日在“文学报”官方公众号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