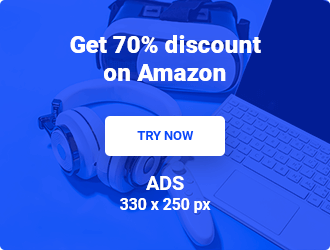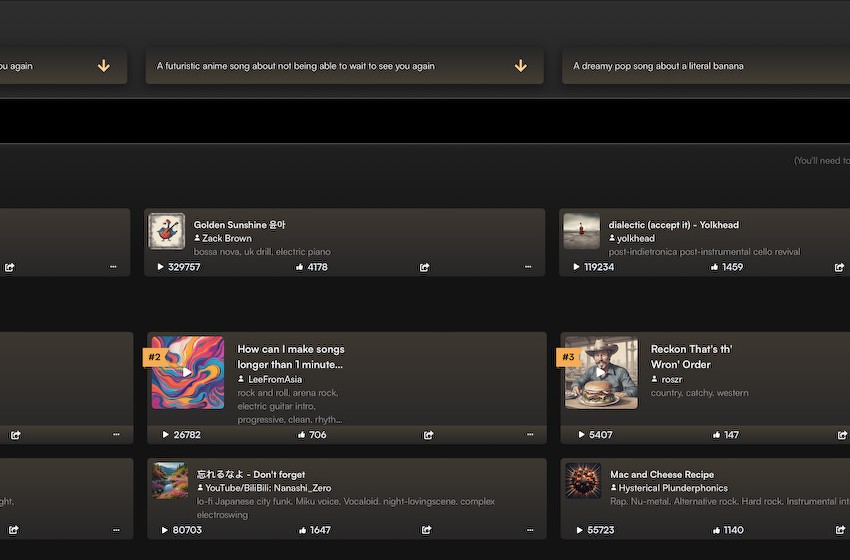专访|导演叶大鹰:25年经典穿越,《红色恋人》依然如新
9月11日,北京,当中国电影资料馆1号厅的灯光亮起,全场掌声。坐在观众席第五排正中,导演叶大鹰脸红扑扑的,两腮上还挂着泪痕。在他身旁,制片人、北京紫禁城影业的老领导张和平感慨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大鹰,这是部伟大的电影。”

《红色恋人》复映海报
作为1998年公映电影《红色恋人》的导演和制片,那一刻,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25年过去了,这部在当年引起极大轰动的“红色”电影,终于从库房蒙尘的胶片盒中取出,由胶片版本转至数字版本,再度回归大银幕,于9月12日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影院专线上映。
“今天晚上,我一边看一边流泪,大鹰坐在我身边,我听到他也哭了。我今天特意穿了件红衣服,这件衣服不那么新,但是它诚恳、真实。”制片人张和平在首映礼的交流环节说道,“同志们啊,这部电影的复映太不容易了,这里面经历过多少沟沟坎坎……我可以写一本书。”
全场再度响起掌声,或许独缺影厅的第九排十二号。

首映礼上,中国电影资料馆1号厅九排十二座留给了哥哥张国荣
这个空着的座位上静静地放置着一捧鲜花,鲜花上摆着一张字条,上写:“祝福哥哥67岁生日快乐!!!致敬经典!!!”它来自有心的“荣迷”。9月12日复映当天,是《红色恋人》主演张国荣的67岁冥诞。
香港明星张国荣饰演中共地下党领袖,叶挺之孙叶大鹰继《红樱桃》之后再导“红色”电影——翻看25年前的报刊,《红色恋人》的报道连篇累牍,却大都不脱前述这两个关键点——而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书写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电影史,似乎都绕不开叶大鹰执导的这两部电影。
先说《红樱桃》。电影于1995年公映,许多观众第一次了解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度过了一段鲜为人知又极不寻常的岁月。而抛开彼时片中主人公楚楚在大银幕上“裸背”的嘈杂争议,那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放在世界影史比较的场域,中国电影人第一次用一部国产电影,将中华民族在海外所遭受的战争创痛与英勇抗暴,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阔历史相连。
而从电影产业的角度寓目,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回忆说:“1992年,《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出台,电影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是从这开始的。之前电影院是文化单位,可以拿政府补贴,产业化之后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没两年中国电影就快活不下去了,所以才有了1994年的分账引进好莱坞商业大片来延续电影市场。刚好在1995年,出了《红樱桃》和《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两部电影的市场表现特别好,观众口碑也高,让整个国产电影为之一振。《红樱桃》在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上辟出了一条新路,它不是按照过去的正剧来拍,而是将革命题材加以浪漫化,改变了红色电影固有的叙事模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

张国荣 饰 靳
1998年,《红色恋人》的热映延续了《红樱桃》的话题性。公映前,围绕电影最大的争议是,能不能让张国荣演一个中共党员?以及他究竟演得好不好?按照导演叶大鹰后来的自述,他当时想反映的人物概貌是早期共产党的形象,会说英语,有文化气质,对物质的感觉很淡。“我考虑到人物的家庭背景所带来的特质,这个在海外华人中比较容易找到,在内地找难度比较大。咱们40多岁的演员,一般都属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那种形象,糙得比较多,但是在文化气质上,真是来自内心的那种表现人格和精神方面的东西不如外面的演员来得细腻。于是就把剧本拿给香港的朋友,请他们物色角色。”
叶大鹰事后坦诚,起初打算由尊龙出演革命者靳,但香港朋友向他极力推荐了张国荣,他们在一起吃了顿饭。“那是我第一次和张国荣面对面,他很有心,来之前应该已经看过剧本了,但他说自己没看。这个人很儒雅,很有分寸,但自尊心极强。而且当天他脸上留了短短的胡茬,柔美里透出一股子沧桑。我给他讲了那些理想主义革命者的故事,讲的都是人的故事。我就发现他的眼神是跟着故事中人物命运的起伏在流转的。这顿饭一吃,我心里就知道这哥们儿行,绝对行。”
9月11日《红色恋人》北京复映首映礼结束后,叶大鹰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叶大鹰
【对话】
那代职业革命者,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最富浪漫情调的
澎湃新闻:我们看《红色恋人》的片名,其实就暗示出这部电影是从革命英雄主义到革命浪漫主义的一次嬗变,请谈谈你是如何看待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毕竟,这部电影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是,“浪漫”。
叶大鹰:在创作、拍摄《红色恋人》时,我们肯定在革命浪漫主义上着墨更多,当年对这部电影的定位是“经典样式的浪漫主题影片”,是在革命英雄主义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革命浪漫主义的银幕回归。
在恢弘壮阔的中国革命中,英雄千千万,我爷爷叶挺身上就更多体现出革命的英雄主义,甚至是一种标杆般的存在。但在党的内部,也有像瞿秋白这样的英雄,他曾被解除过领导职务,被边缘化,但在面对敌人枪口的时候,如果他的信念稍微有所动摇,可能就能活命。但就像是电影中靳的台词,“如果我不能骄傲地活着,那么我选择死亡!”其实不仅是瞿秋白,还有毛泽民等等,我听过太多英烈在严刑拷打面前,在屠刀面前坚贞不屈的故事,真是听得热泪盈眶。

《红色恋人》剧照
澎湃新闻:电影中靳的牺牲是正面直对敌人的枪口,这和瞿秋白选择就义的方式是一样的。
叶大鹰:展现烈士就义,对于导演而言是个特别大的难题,前面已经有了《刑场上的婚礼》《烈火中永生》。从我这代人的想法,当时我还不到40岁,就在琢磨怎么拍出不一样的呈现,比用一句口号更有力量。
这里面有瞿秋白的影子,他是昂首走向刑场的。一路上,他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在一块草坪上,盘腿而坐,面对敌人枪口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此地很好!”据说他当时还告诉刽子手,“不要打我的脸。”瞿秋白是一位内外都追求高洁的人。而且,他和妻子杨之华之间的爱情故事,包括他去上海养病(肺结核)这些经历,也都融入了电影的情节。
片中靳是坐在椅子上面对枪口,这点上我们参考了吉鸿昌就义的情形。当时拍的时候是大冬天,张国荣手上、脚上的大铁链子是真的,我告诉他除了全景、特写,拍不到他的时候可以取下来,但他就要一直戴着,一直沉浸在那种感觉里。我们是用高速摄影拍得干脆利落,枪响,靳一下子翻倒,空中他的肢体和铁链子呈现出一个“工”字形。这个画面肯定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有冲击力。

《红色恋人》剧照
澎湃新闻:你曾经说过是在筹备《红樱桃》时听到了很多父辈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中的哪些特质、细节,促成了你要拍《红色恋人》?
叶大鹰:我一直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职业革命者,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最富浪漫情调的。如果在一个常态的生活环境下,大家都有很现实的家庭,可怎么这帮人就干了革命了?比如彭湃来自一个封建家庭,分家产参加革命。如果你把他当作一个人去看就能体会到他的种种难处,他要面对家庭,怎么去割舍血缘亲情?
在创作《红樱桃》的过程当中,我们采访了差不多三十多位革命烈士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子女,听他们讲当年的经历,也包括爱情故事。《红色恋人》中靳和牺牲的妻子是在法国留学时结识的,这里面有当年留法那批早期共产党员的事迹。但这并不是非要对应到原型,太多的故事弥漫在我的潜意识里,变成一种非要拍出来不可的情感。
从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革命,并不是我们的首创
澎湃新闻:谈谈剧本创作,是你把这些故事口述给编剧江奇涛,他来执笔吗?
叶大鹰:其实是我们仨,我和编剧江奇涛、摄影师张黎一起听故事,都觉得必须要拍一部这样的电影。从我的电影处女作《大喘气》,就和张黎是开始合作,那时他就担任摄影。《大喘气》拍出来后,社会上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我这才铆足劲要拍“红色电影”。江奇涛在80年代就是知名的军旅作家了,张黎和江奇涛是好朋友,他把江奇涛介绍给我,大家一起合作了《红樱桃》,我们仨这么一路下来。
最初的想法是拍一部《红色女人》,想写一个共产党红色家庭的三代人,三代女人间的故事。写着写着,男性角色靳被凸显了出来。可以说《红樱桃》拍完之后,我们就已经做了《红色恋人》的心理案头。

《红色恋人》剧照
《红色恋人》里那些精彩的台词,那些展现人物价值观和信仰的,特要劲儿的台词都是江奇涛写的。我最喜欢里面他写的那句,“如果我不能骄傲地活着,那么我选择死亡!”包括靳在火车头旁宣讲革命,第一句话“我们跟蒋介石先生打了十来年的交道,深知其人其道。”这是他模仿了毛主席、周总理后来接见外宾时谈到蒋介石的口吻。他是把我们感慨、感动的故事真正形成于文字,落实在剧本上,我更多地是在讲述的角度上去拍板下决心。
澎湃新闻:《红色恋人》的故事视角是由片中的美国医生佩恩来讲述的,这点上是谁的主意?
叶大鹰:这是我们大家在开剧本会时提出来的,不谋而合想到了如果这个故事是通过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国家的人士讲出来,那会更有力量。其实从外国人的角度来讲述中国革命,并不是我们的首创。从史沫特莱到埃德加·斯诺,当年很多这样的外国友人、记者通过他们的报道和笔触,讲述中国革命,展现中国红军和党的领导者。你会觉得他们的角度讲述出的故事特别令人动容,而且毕竟我们离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已经很久了,他们的讲述会让观众更有代入感。

《红色恋人》剧照
澎湃新闻:在电影片头字幕阶段,我看到两位美国编剧也加入了剧本的修改。是不是正是有了佩恩这个角色,你才会去找到美国编剧介入剧本?
叶大鹰:没错,既然是美国人来讲这个故事,那要遵循美国人讲故事的习惯和方式,包括台词的顺序、讲出来的口吻和语境设计。《红樱桃》出来后,也在美国有过放映,包括参加评奖,好莱坞的制片人也曾约我拍电影,就这样朋友介绍朋友,我也认识不少美国编剧。
第一个介入进来的编剧马克·卡普林,我把他请到了北京来,他其实是制片人出身,修改了一遍我还是不大满意。之后我专程去了洛杉矶,找到职业编剧安迪·南桑森。这是位女士,我和她用了差不多一个月来改剧本。好莱坞编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每一个词、每一个空当都要问你为什么。然后我就给她解释。这种“逼迫”给我的好处特别大,知道了他们的那种思考习惯和对台词的处理方式。

《红色恋人》剧照
澎湃新闻:能具体举个你们间碰撞的例子吗?
叶大鹰:中文跟英文间有很大的差别,背后更有民族思维方式和习惯的差异。你比如剧本中,靳讲述他和妻子的往事,“我们在巴黎相识,我是因为她的引导参加革命的……”安迪就会问,“引导”这个词应该是《圣经》里的,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同时她也认为一个男人走上革命道路,真的就是受一个女人影响的结果吗?我就得跟她讲,在我们的革命者当中有很多夫妻搭档,他们就是互相影响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
还有在“……直到她死,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上,安迪也不明白,问我为什么妻子死了以后靳才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呢?他对革命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互相掰扯的过程,挺让我闹心的,但我逐渐随着她问的问题,把每一个人物的历史、经历全部都梳理得特别清楚,这给后来拍摄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包括现场给美国演员讲戏也都非常顺畅。
我可以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红色恋人》公映后,美国大使馆的人曾经找我,求证片中佩恩的原型到底是谁?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他,这是我们编的(笑)。但这不是胡编乱造,他身上带有史沫特莱、斯诺的影子,片中佩恩的身份不仅是个大夫,也给美国的报纸写报道。
澎湃新闻:电影里靳一旦发病,秋秋都会给他读一首俄罗斯文学的诗歌,“太阳出来了,一只鹰从地面飞向天空,突然在半空中停住,好像凝固在半空中,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飞,为什么停住……”这首诗是莱蒙托夫写的吗?我们查不到。

《红色恋人》剧照
叶大鹰:你们肯定查不到(笑)。这个情节的源起来自周总理得癌症后期,特别疼的时候就念毛主席的诗词,真的出处就是这样的。靳发病时念的那段台词是我们杜撰的,模仿了莱蒙托夫的笔法。靳与妻子都在法国留学,但如果在这里念法国作家的东西就会给人很“隔”的感觉,选择俄罗斯文学,我对那样的真实感有把握,何况我们这一代人又都有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情结。
当时我们在现成的作品里挑来挑去,也找不到既特别感人又照应情节的一段话,后来是江奇涛看得多了,干脆自己揣摩历史语境写了一首,放在电影里。包括电影里那本俄国文学“刊物”也是我们自己做的,特别唬人。这么多年下来,不知道有多少俄国文学的爱好者向我求证这事,甚至有俄国人也找来,问我摘的这首诗到底是谁写的?搞得我哭笑不得。
张国荣这样的演员,不仅懂戏,更懂情感
澎湃新闻:回到电影,靳是一位革命者、地下党的领袖,过往这样的人物出场往往会有任务导向,而电影中的靳来到上海只是为了治病。电影中是通过秋秋的回忆,她怎么爱上了靳、崇拜靳,是在现场看到了靳在火车头旁激情的演讲。这段情节是电影一大亮点,也是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一处完美结合。

梅婷 饰 秋秋
叶大鹰:我们不能去小看观众,对于那段历史,观众其实都了解,而电影人要拍一部电影,它必须是用心去理解、感受后,一定是带着感情非把它拍出来不可,得有这股劲儿才能拍出好电影。我是认为电影中的每场戏都不能割裂开来去贴标签,好的电影,乃至那些古典主义文学、戏剧作品,不会在一场戏里只单一解决一个问题,都是前后呼应、上下贯通的。
我后来也拍过《陈赓大将》,他是在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右腿负伤,不得已去到上海治病。包括刚才提到的瞿秋白也曾去上海治疗肺结核。其实当时很多在反围剿,包括长征途中受伤的早期领导者都曾去到上海治病,当时也只有上海有这样的医疗条件。另外上海特科里面的柯麟大夫,大学就是学医的,等于说他既是个能锄奸的特工,又会给人看病,他在上海开的诊所也是一个交通站。
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肯定要找个火车头,这是有代表性的意象。拍摄当天张黎还发着高烧,但也在坚持。张国荣那一大段台词分解成几个部分来拍,每一段结束,现场群众演员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在片场有个习惯,拍完一场戏第一个目光都会投向我,我觉得不错了,他还是会蹲在监视器边看一遍回放。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很多场戏都拍了三四条,一定是挑状态最准确的那条。当他最后攥着拳头说完那句,“他们的名字叫红军!”现场欢声雷动,我大喊“过了,过了!”他如释重负地说了句,“完了吧。”然后双手抱拳举过头顶向大家鞠躬致谢。

《红色恋人》剧照
澎湃新闻:关于张国荣的演技,在片场给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
叶大鹰:他的表演经常会让我震惊。比如片中秋秋给靳留了一封信,张国荣在念信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特希望你在念的时候眼泪涌出来了,但要停在眼眶里,念到最后眼泪还得给收回去。我告诉他,这是我对革命者情感的理解,儿女情长就得收在这儿。那个镜头拍了三遍,其实第一遍他就做到了,真的是能抻得住,可他还是想再试一遍,觉得自己还可以演得更好。
《红色恋人》之前,张国荣已经演了七十多部戏了,演技可以说炉火纯青,而且他是一个特别内秀、走心的演员。当初第一次见面我给他聊剧本,就发现他的眼神是跟着故事中人物命运的起伏在流转的,当即就决定靳这个角色非他莫属。我不否认,创造角色需要体验生活,但这种体验也有多种方式,不是当了党员才能演党员,当了皇上才能演皇上。演员可以有许多接近角色、借鉴情感的方法。张国荣就是这样的演员,不仅懂戏,更懂情感,他是在用生命来诠释角色。
电影拍完后,张国荣在戏里穿的长衫,我送给他了,他说要拿回去好好收藏。他离开我们20年了,我还是会时不时想起他——电影中靳在讲述妻子牺牲时有句台词,“那楼很高,她在空中坠落的时间很长,那情景很像一本俄国小说当中的描述。”后来也有朋友问我,这和张国荣一跃而下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太像了?我是觉得,他是被抑郁症病魔带走了,在他无法骄傲地活着的时候,选择了死亡。我自己也得过抑郁症,经过了几年才恢复过来,所以特别理解人在绝望时的情绪。抑郁症没有那么明晰的因果,它就是一种可怕的疾病。
澎湃新闻:谈谈梅婷和陶泽如饰演的这对父女。秋秋这个角色并不好演,在靳的面前,她时而像是学生,时而又是恋人,在安抚靳的时候又要展现出母性的光辉,而皓明也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叛徒。
叶大鹰:梅婷当时还是前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之前演过电视剧《血色童心》(剧版《红樱桃》)里的楚楚。我觉得张国荣特别会给戏,她跟他一块拍戏时,没有感觉到那种明星的架子,感觉还是很默契的。《红色恋人》公映后在上海开研讨会,我记得张瑞芳老师发言时就说,秋秋让她想起了自己17岁入党时的情形。

叛徒皓明在敌人的威逼下,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志
陶泽如当年主演《一个和八个》的八路军角色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次我请他演叛徒,他饰演皓明这个角色,很容易让人想到顾顺章——我看过很多叛徒的回忆录,有的人也不是一进去就变节了。所以在塑造皓明时,在他身上加入了一些宿命的色彩,更文艺化了。在这样的故事里人性为大,观众要看的是人性和信仰的冲突,而他的背叛和靳的坚贞也构成一组对比关系。
其实这部电影对他们两位的难点是有大段的英文台词,梅婷、陶泽如都是现学现教的英语。演员大都是提前两个月进组,梅婷进组更早一些,开拍前台词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有些人认为陶泽如说的英语很艮,但很多老外认为,戏里皓明说的英语就应该是这样。
澎湃新闻:电影故事的背景设置在1936年的上海,从置景和美术的角度,当时有哪些着眼和强调?
叶大鹰:我们的美术师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老美术师钱运选,在业内很有名,电影开头的酒吧戏份是在车墩搭的景。片尾秋秋击毙皓明那部分,是在外滩12号汇丰银行大楼旧址拍的,1923年的老建筑,内部是用大理石、黄铜作为装饰材料,非常富丽堂皇。当时这幢大楼正要改为浦发银行总部,负责人正好是《红樱桃》的影迷,答应借出一层楼让我们拍,很多场戏都是在里面拍的。
一部电影呈现出的画面和气质要符合时代,在这点上,我还是很满意的。《红色恋人》上海研讨会,谢晋老爷子在洗手间和我开玩笑说,“我们上海电影人一直想拍老上海故事,怎么让你个北京小子拍出来了。”我用上海话回答他,“阿拉上海宁,哈哈。”我在上海生活过,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技校,对上海过去的味道还是有点感觉的。
澎湃新闻:这部电影时隔25年再次上映,观众已经迭代,你希望当下00后的观众如何解读这部电影?
叶大鹰:这次重映路演期间,让我特别触动的就是年轻观众,映后互动时很多00后的女孩子,站起来说不出话还在哭……他们这代人能被剧情打动,让我觉得这部电影依然很新。它里面很多东西穿越时空依旧能直击人心,年轻观众会在大银幕上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张国荣,一个意想不到的红色爱情故事。

《红色恋人》剧照
澎湃新闻:影片最后你用了一种蒙太奇的手法:1949年,靳和秋秋的女儿小明珠从父母的骨灰盒中拿走了父亲身体里残存的弹片,随之俯拍的镜头下看似现场“穿帮”了,却穿越回到了1997年外滩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附近,随之又给了对岸浦东陆家嘴一个大全景。我想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致敬。
叶大鹰:你这么理解当然是对的。我不想把这部电影说得太白了,观众走进影院自然会有自己的读解。好电影是什么样的?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有个老师曾说过,如果用口号或者用嘴巴就能把故事说得明明白白,或者用文字就能写明白的,那还拍电影干嘛?好电影通过蒙太奇带给观众的观感是整体的,是用电影的语言给人一种心里明白却说不清、道不明,无以名状的感受。

电影中小明珠的饰演者叶丹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